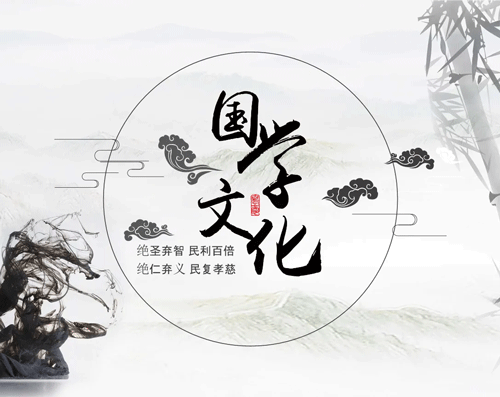陆游诗歌中的殊像 [马新广]
发布时间:2024-09-27 16:19:04作者:地藏网陆游诗歌中的殊像
马新广
陆游诗歌中常用佛典来抒怀,有一些富有禅趣的诗句。如《出都》: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野寺》:去来元自在,宾主两相忘。等等。这些富有禅意的诗句在全诗中已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而是和全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种任运随缘的态度。在这些诗歌中,陆游把佛学理论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人生修养和思想品格。有了这种思想修养,那些佛教理论和言语就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与点缀,不再仅仅是直白生硬的说教,而成为内在的立意与构思,它们和一定的形象相结合,就成为富有悠长韵味和意义的作品。
佛教虽是出世的宗教,但为了适应华夏社会的传统,也适当接受一些儒家的教义。陆游在《高僧猷公塔铭》里说到高僧子猷——
虽浮屠其衣,百家之书,无所不读。闻名儒贤士,虽在千里之远,必往交焉。
《别峰禅师塔铭》说别峰禅师——
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从之游。……圆悟再传,是为别峰。十坐道场,心法之宗。渊识雄辩,震惊一世,矫乎人中龙也!海口电目,髦期称道,卓乎洞壑松也!叩而能应,应巳能默,浑乎金钟大镛也!师之出世,如日在空。隐于崦嵫,其可以为终乎。
可见宋代禅师把佛理与儒家学说加以互参融合的时尚风气,禅师与儒者的切磋和来往也成为有宋一代的普遍现象。
从陆游有关佛教内容的诗歌中,首先可以看出佛教对陆游诗歌风格的影响并不明显,对其思想和生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虽然陆游常常参禅,频繁地和禅师交往,家里也有佛像和禅室,也有最基本的佛教语汇以及幽微的佛教观念的影响踪迹,他对佛教的浸润始终不如苏轼那么深厚。而且在陆游的作品中体现禅意或禅趣的作品并不罕见,纯粹论说佛理的诗歌也不多。即使他那些最富禅意的作品也很少完全体现出明净淡远、枯淡空寂之风神。在陆游退居田园后,在他人生的晚年,佛教思想也并不突出,诗歌风格也没有体现太多的禅味。陆游对佛教之接受,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严羽提倡诗人要多读书,多穷理,增加修养,才能写出好诗。佛教发展到宋代,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宗教的范围,而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状态。陆游对佛经的大量涉猎,正是把佛教知识作为加深其学问修养的途径,并以之作为诗歌创作的题材。陆游和佛教的因缘,在诗作中明显的呈现是游览寺院和交往禅师。有宋一代,禅净二宗最为流行,在佛教文化繁盛的情况下,游历寺院、结交僧人是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位诗人都会有此类作品。即使与佛教无甚因缘,也可做僧寺之游,留下一些风雅文字。寺院是佛教明显的社会存在,寺院对世人来说往往会引起对佛教义理的联想。但陆游却并非如此,他感受到的往往是世事如烟和人世的变化沧桑,几乎纯是人世间的感慨,但这种感慨又是在佛教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次,陆游对佛教的涉猎是由于时代风气使然。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不断改造后,成为中国盛行的两大主要宗教之一。自汉魏以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苦读儒家典籍,又习佛家之说,与僧人来往密切,他们行走在仕途官场和山林庙宇之间,穿棱于儒家和佛教的思维之域,优雅而又从容。满怀着儒家人世的热情和道义,又时常高谈着人生的空幻,渴慕着幽寂的山林,成为士大夫典型的生活范式。唐宋时期这种社会风气尤甚,陆九渊、陈亮、叶适曾经批评朱熹出入佛、老,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而朱熹反过来这样批评他们。可见当时士人对佛教思想的浸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南宋诗人代表的陆游也不例外,他大量涉阅佛教典籍,来往于寺院和僧人之间,这种景观弥漫在其整个生活和作品中,但士大夫们对佛教的参与,只是停留在理性、冷静的观照层面上,没有把自己的整个人生投入到狂热的宗教信仰中去。他们只是要从佛教的哲理中来加深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并从中达到一种超越形迹和现实的心灵自由,使精神从现世的炎凉和社会政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被认为浸佛颇深的苏轼在《与参寥子书》中就说——
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世态人情炎凉,把苏轼推向了空门。
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结合导致了士大夫与僧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在宋代禅宗盛行的文化氛围,上人与禅师的交往,进而在其作品中留下去佛教的痕迹是普遍的现象。陆游正是这样的的人物,他和众多禅师的交往也是佛教文化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表征之一。陆游与禅师的交往,主要是酬答赠言,赞美其道德高风,或谈及诗艺,而很少和他们论禅理。陆游和那些具有高尚品德和坚毅精神的禅师们交往,为他们作塔铭和真赞,一方面是因其言行风采卓异特出,另一方面也是借高僧们的优良品德来抨击当时士大夫的软弱和衰弊的世风,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再者,陆游的悦禅借参禅寻幽息虑,缓解人生的烦恼,寻求心灵的平静。如《天竺晓行之二》云——
笋舆咿轧水云间,
惭愧忙身得暂闲;
堪笑风中一黄叶,
知看天外几青山。
日本当代专攻禅宗史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东方部教授柳田圣山(1922——2006年)在《无的探求(中国禅)》一书中说—一
禅者,专注于精神的宁静,在林中漫步,在树下冥想,会感到极大的满足。让心灵宁静,不要彷徨,不要后悔,不要怠慢,修行者应该去寂静的地方栖身。
陆游在他仕途较为失意、人生处于低谷的阶段,经常频繁地造访寺院和禅师。而且他到寺院经常栖息于禅房之中,心境安宁,使在尘世中焦虑不安的精神得到休息。他要借助禅院的幽寂与禅境的空静来消解内心的痛苦和郁闷。他在《寓天庆观,有林使君年八十七方烧丹》中说:世路崎岖久已忘,道腴禅悦度年光。道山了陆游一生参禅的真实想法和目的——他之悦禅只是为了度过他那心在天山但却身老沧州的失意岁月。
综观陆游的一生,一直受到当权的南宋投降派的压制,空怀壮志,报国无门。他在积极慷慨鼓吹抗战的同时,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其中自然也包括禅师羽士。当时宋朝皇室十分尊祟佛教,故他也与僧人们过从甚密。尤其在他郁闷不得志的时候,更对佛教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志则泽加于民,不得志则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避世远害,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明哲保身,甘于淡泊,乐道安贫,不屑与人情叵测的污浊社会共处,厌恶病态社会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思欲隐遁山林田园,养性全寿。养成了随缘任运,安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摘自《空林佛教》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