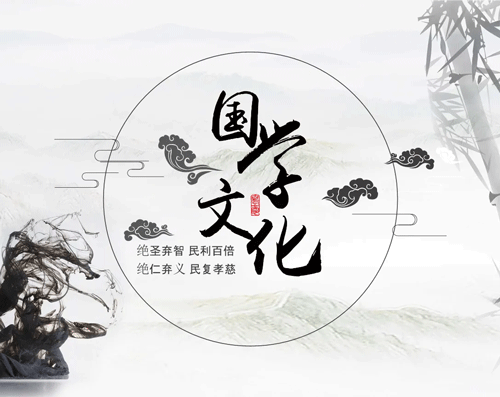陈士强教授:《阅藏知津》要解 上
发布时间:2024-10-12 12:40:55作者:地藏网陈士强
《阅藏知津》,简称《知津》,总目四卷、正文四十四卷,合四十八卷。清顺治十一年(1654),北天竺沙门智旭撰。收入《法宝总目录》第三册。智旭,字蕅益,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初习儒学,辟佛老,着《辟佛论》数十篇。十七岁时,因阅袜宏《自知录》和《竹窗随笔》,遂不谤佛,并取前论焚之。二十四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后游江、浙、赣、闽、皖诸地,晚年入居灵峰(在浙江孝丰)。生平着述五十一种,其中重要的有《楞严经玄义》、《楞严经文句》、《法华经会义》、《起信论裂网疏》、《八识规矩颂直解》、《教观纲宗》、《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等。弟子成时将其著作分为“宗论”和“释论”,而将宗论类著作编成《灵峰宗论》十卷,书首有《八不道人传》,叙说智旭的生平事迹。
《知津》书首有智旭自撰的《叙》、夏之鼎撰写的《缘起》和智旭介绍《知津》体例的《凡例》。
智旭《叙》云:
“顾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刹所供大藏,不过缄置高阁而已。纵有阅者,亦罕能达其旨归,辨其权实。佛祖慧命,真不啻九鼎一丝之惧。而诸方师匠,方且或竞人我,如兄弟之阋墙;或趋名利,如苍蝇之逐臭;或妄争是非,如痴犬之吠井;或恣享福供,如燕雀之处堂。将何以报佛恩哉?唯宋有王古居士,创作《法宝标目》,明有蕴空沙门(寂晓),嗣作《汇目义门》,并可称良工苦心。然《标目》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尽美;《义门》创依五时教味,粗陈梗概,亦未尽善。旭以年三十时,发心阅藏,次年晤壁如镐兄于博山,谆谆以义类诠次为瞩。于是每展藏时,随阅随录,凡历龙居、九华、霞漳、温陵、幽栖、石城、长水、灵峰八地,历年二十,始获成稿。”(《法宝总目录》第三册,上、中,下同)
《叙》中所说的“始获成稿”,指的是《知津》大体告成。因为书末叙载的属于此方撰述中的“序赞诗歌”三种和“应收入藏此土撰述”四十五种,当时仅载书名,尚无提要。据《叙》末所署的年月,其时为“甲午(1654)重阳后一日”,仅隔三个多月,至翌年正月二十一日,作者便去世了。最后补充进去的这些著作,也就无人补写提要了。九年以后,至清康熙三年(1664),夏之鼎等人抽资依原稿刻印流通。光绪十七年(1891),金陵刻经处校对重刊,在《知津》最后叙载的四十八种著作的题名下添注了撰者名氏。收入《法宝总目录》的即是此本。
《知津》将全部佛典分为四藏:
第一经藏下分大乘经和小乘经。大乘经分为五部:华严(卷一)、方等(卷二至卷十五)、般若(卷十六至卷二十三)、法华(卷二十四)、涅槃(卷二十五)。这中间方等部又分为显说(卷二至卷十)和密咒两部,密咒部再分为经(卷十一至卷十四)和仪轨(卷十五)两项。小乘经(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不分部。
第二律藏下分大乘律(卷三十二)和小乘律(卷三十三),末附“疑似杂伪律”一部,即《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一卷(西晋失译)。
第三论藏下分大乘论和小乘论。大乘论分为释经论(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宗经论(卷三十七至卷三十九前部分)、诸论释(卷三十九后部分)三类,每一类又分为西土和此方两项;小乘论(卷四十)不分类。
第四杂藏下分西土撰述和此方撰述。西土撰述(卷四十一)不分类,末附“外道论”两部,即《胜宗十句义论》一卷和《金七十论》三卷,又附“疑伪经”一部,即《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二卷;此方撰述(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分为十五类:忏仪、净土、台宗、禅宗、贤首宗、慈恩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应收入藏此土撰述。这中间“应收入藏此土撰述”又区别为释经、密宗、净土、台宗、禅宗、慈恩宗、纂集、传记、护教、目录十项。
《知津》所解说的佛教经典究竟有多少,作者没说,书中亦无可资参考的统计数。不过,由于《知津》所解说的经典囊括明南藏(《永乐南藏》)和北藏(《永乐北藏》),于此入手,可以推知。据《法宝总目录》第二册所刊二藏目录,南藏收佛典一千六百一十部,北藏原有佛典一千六百一十五部,万历十二年(1584)又将汉地撰述三十六种,编为“大明续入藏诸集”合入,成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叠合的部分不计,明南北藏收录的佛典总数为一千六百五十七部。《知津》将其中的《感应歌曲》合入《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称歌曲》,作五十一卷,从数目上减去了一部。另外新增明藏所缺的《维摩诘所说经疏》十卷、《维摩诘所说经记》六卷、《六妙门禅法》一卷、《释摩诃衍论》十卷、《肇论》一卷、《观心论》一卷等六部,以及“应收入藏此土撰述”中所列的四十七部,则《知津》着录的佛典为一千七百九部。
自北宋至明末出现的《大藏经》解题(或称提要)著作中,《知津》成书最晚。

《知津》在分类方面的特色:
一、按天台宗五时判教编排经藏。
此种编法发轫于寂晓所撰的《义门》,彼书打破了宋元大藏经均依《开元录》分类编次的规式,根据天台宗的五时判教,将全部藏经编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着述九部。《知津》在《义门》的基础上损益取舍,更成一体。历来经录均将《般若经》放在大乘经之首,而《知津》则置《华严经》为大乘经之首;将《开元录》中宝积、大集两部,与五大部外诸大乘经(包括重译和单译)的大部分经典合在一起,成立方等部;将《法华》从五大部外大乘重译经中独立出来,并附以性质相近的数部大乘经,成立法华部。“《义门》但分五时,不分三藏,谓三藏小教,但属阿含一时也。”(《凡例》,第1007页下)《知津》仍按历来的典则,将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义门》在华严部以后叙阿含部,这虽符合五时的顺序,但作者认为,“以小教加于方等、般若之前,甚为不可。”(同上)因此《知津》仍依经律论三藏的每一藏先大乘、后小乘的原则,将《阿含经》移至法华、涅槃之后,即叙完大乘经之后,再叙小乘经;《开元录》中的密教经典是按其重译或单译被编入“五大部外大乘重单译经”中的,《义门》将密教经典抽出,单独编为一部,而《知津》参照《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法,将密教经典看作是大乘经的分支,将它编入方等部,并剖分为密咒经和密咒仪轨两项。
二、第一次将大乘论藏分为释经论、宗经论和诸论释三类,并将中国僧人有关的章疏论着编入其内。
在《开元录》以前,大乘论是不分子目的,《开元录》根据大乘论的内容有疏解某经和通论教义的不同,创立释经论和集义论的分类法,然而所收仅限于印度的佛教着述。智旭在《开元录》的基础上,别创三分法,即在释经论之外,将“集义论”一类再分为宗依大乘经文、阐释大乘义理的“宗经论”和对大乘论进行解释的“诸论释”,这就更符合大乘论的实际构成。而且智旭在大乘论三类的每一类中,不仅收印度佛教学者的著作,同时也收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这是以往经录中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土大乘释经论”中收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六十卷、法藏的《华严经指归》一卷、宗密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之钞》三十卷、明宗泐和如玘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八卷、隋智顗的《四教仪》六卷、宋子璿等的《首楞严经义海》三十卷等三十八部;“此土大乘宗经论”收姚秦僧肇的《肇论》三卷、隋智顗的《摩诃止观》二十卷等十四部;“此土大乘诸论释”收元普瑞的《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宋知礼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六卷、宋师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连珠记》二卷、唐窥基的《大乘百法明门论解》一卷、元文才的《肇论新疏游刃》二十卷、唐湛然的《止观义例》二卷等二十一部。
三、开立杂藏。
杂藏之名,源自经文。智旭说:“若据《智度论》说,则凡后代撰述合佛法者,总可论藏所收。若据《出曜经》说,则于经律论外,复有第四杂藏。今谓两土著作,不论释经、宗经,果是专阐大乘,则应摄入大论;专阐小道,则应摄入小论;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间,二论既不可收,故应别立杂藏。”(《凡例》,第1007页下)简而言之,杂藏所收的是大乘论和小乘论所不能包括的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撰述。《知津》又按宗派、文体、内容和新收诸方面,将“此方撰述”即中国佛教撰述分为十五类,收录著作一百八十一部,这种慎细的分类是前所未有的。
四、调整经典的归属。此有种种不同:
第一,大乘经的调整。如《圆觉经》一卷(唐佛陀多罗译),在《开元录》中属于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知津》则将它移至华严部;《大乘方广总持经》一卷(隋毗尼多流支译)及其异译《佛说济诸方等学经》一卷(西晋竺法护译)、《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及其异译《等集众德三昧经》三卷(西晋竺法护译)、《摩诃摩耶经》二卷(萧齐昙景译)、《大方等大云经》四卷(北凉昙无谶译)等六经,原属五大部外大乘重译经。《菩萨处胎经》五卷(姚秦竺佛念译)、《中阴经》二卷(同译)、《佛说莲华面经》一卷(隋那连提黎耶舍译)等三经,原属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知津》均编入涅槃部。
第二,将有些大乘经编入大乘律。如《开元录》定为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的《舍利弗悔过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及其异译《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卷(隋阇那崛多译),《知津》勘同《菩萨藏经》一卷(萧梁僧伽婆罗译);《菩萨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知津》勘同《菩萨戒本经》一卷(北凉昙无谶译)和《菩萨戒本》一卷(唐玄奘译);《文殊师利问经》二卷(萧梁僧伽婆罗译),原属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佛说善恭敬经》一卷(隋阇那崛多译)及其异译《佛说正恭敬经》一卷(元魏佛陀扇多译),原属五大部外大乘重译经。上六经,《知津》均编入大乘律。
第三,将有些大乘经移编为小乘经。如《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一卷(姚秦罗什译)、《佛说法灭尽经》一卷(刘宋失译)、《般涅槃后灌腊经》一卷(西晋竺法护译)、《天王太子辟罗经》一卷(姚秦失译)、《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一卷(唐义净译)等六经,《开元录》编在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之中,《知津》均编入小乘经。
第四,将有的大乘论编入小乘论。如《缘生论》一卷(隋达摩笈多译),《开元录》编在“大乘集义论”一类,《知津》则编入小乘论。
第五,将有的小乘经编入小乘律,如《佛说斋经》一卷(吴支谦译),本为《中阿含经》第五十五卷的异译,《知津》将它编入小乘律。
五、同一类经典中的单本和重译,根据内容加以编次,并在重译中选取善本加以标识。
《开元录》以前的经录在叙述同一类经典时,都是先叙单本,后叙重译,至《开元录》则反之,先叙重译,后叙单本。寂晓的《义门》采用《开元录》以前经录的办法,在重单译中,先取单本总列于前,后以重译别列于后。这两种编法有条理清晰的好处,但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毛病,即“相去悬隔,查考稍难。”(《凡例》,第1008页上)以《开元录》卷十二所收的密教经典为例,一部分出现在五大部外大乘重译经中,另一部分又出现在五大部外大乘单译经中,中间隔着数十部虽是重译但因阙失只存一本的显教重译经和自古以来只有一译的显教单译经。查考之时,自然不便。《知津》别开生面,将单本和重译混编于一处,使内容相近的经典免于分散。
又,以往经录在编定重译的次第时,一般都以译出时间的先后为序,这对于历史状况的真实记叙,无疑是正确的。但重译既多,若一一俱阅,既费时日且无多大必要,故须有人指示何本为善本,以便读一本而得数本乃至数十本重译的要旨。《大唐内典录》曾尝试做过这种工作,它在重译中选取一个好的译本作为诵持的主本,编成“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因选取的译本有些未必真善,招致《开元录》的讥议,以后便无人敢于问津了。《知津》继踵《内典录》之业,在重译中“选取译之巧者一本为主,其余重译者即列于后。”(同上,第1008页中)凡重译经主本和单译经全顶格书写,非主本的重译经“于总目中,即低一字书之,使人易晓。”(同上)并且在非主本的重译经的解说中,指出该本与主本的同异情况,使人知道是否应与主本并读,或者可以不读。这是《知津》的学术价值之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