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者的灵魂
发布时间:2019-11-13 09:14:41作者:地藏经结缘网至今我还不时地想起雪绒山谷,每想起就感到了它的深不可测。几年来三番几次前往,终于也没有读透它。这里的宗教源流、历史人事、神话传奇和民间生活就如同多年生的灌木盘根错节,枯荣流转而生生不息。即使是偶或驻足于此间的云,掠过山谷的风,也都被陶冶得富含文化了。 更何况这里的僧俗,甚至途经此地的人。 十月中旬再去雪绒山谷,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作曲蔡梅孩和音乐顾问边多他们都来采风,就组成了两辆车、九个人。我们是在一个迟暮时分到达的。沿雪绒河款款上行,河岸山坡最后的秋色金灿灿地沐浴在夕辉中,小片阔叶林在海拔高度所能允许的极限处妩媚地招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在身后的烟尘中。渐渐消失的还有金黄秋色。往上走,红得深重的灌木丛取代了杨树和柳树,在山谷深处弥满了高坡,欣欣向荣。 气候也明显地不同于有杨树生长的地方。公历十月的天气不时有雪。早起仰望直贡堤寺所在的山,山半腰以上为白雪所覆盖。堤寺犹如一艘巨轮泊在雪海上。河谷上空风云变幻,朗朗晴空里忽然就涌出了灰色的云,就刷拉拉地下起了雪。通常是小小的雪粒,清凉地落在头上脸上。在这个时候眼睛要眯起,脑袋要缩起,也都拥有了一种清清爽爽的好心境。 我们就不时地在这样的雪天雪地里赶路,上山,采访,站在某个山头眺望我们的雪绒河谷,哪儿宽阔而茫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也不见山谷平地上罗布桑布他们的帐篷。那时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几天了。 这一天不是下雪粒,而是飘起了雪花,是中雪。计划中的拍摄内容需要等待时机。何为和孙亮就驾车出去拍雪景,空镜头。我则陪着两位专家去咱塘村,说是采民歌之风,其实是采了民俗之风和民间信仰种种。咱塘女巫降神时所唱“下部为龙体,其上为人身,手持红色旗,颈插三角旌,坐骑一匹狼,以蛇为僵绳”就是这一次采集到的。这一次虽然欲访努巴活佛未遇,但却获知了他将于一个月后的藏历九月十九日在此地举行金赛仪式的消息。 中午我们沿着积满新鲜白雪的路班师回朝。忽见前方我们的人和车与另一些人混在一堆,闹闹嚷嚷的。把车停在近旁,人们又一齐拥了过来。为首的一位汉子突然用汉话清晰地发问,你就是马丽华吧? 我就这样认识了他,罗布桑布,这位即使在苦难风尘的朝圣路上也保持着清秀风骨和飘逸神采的青年僧人。认识了他的父母和伙伴们。与他们的相遇绝不仅仅意味着增添了一些个拍摄内容。他们之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我们完成了《朝圣部落》这一电视专集后也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而他的父亲桑秋多吉所唱的一首歌,被梅孩用电脑处理过,用电子合成器加了混响和拟人的和声,做了我们十二集《西藏文化系列》的片头歌之后,这一不解之缘算是进一步显示。此刻,距离我们相遇那天近一年,又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地,但仍能触觉到那一线隐隐的缘分。 罗布桑布也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没找到马,碰上了电视。 ——我们在咱塘村的收获大着呢,我向同伴们炫耀说。 无论怎样,何为自豪地宣布,无论怎样,也不如我们的收获大。 他们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雪野上游荡,有什么好看的都拍一拍。牛群在雪地上就如沉静的群雕。雪落在牛身上不再融化,渐堆渐厚,仍然黑白分明。那些形象反映在照片上和屏幕上的时候,格外的质感,象油画。那是罗布桑布他们的驮牛。当镜头从牛身上摇到四顶小帐篷,从小帐篷里又走出了人,他们不免好奇地走了过去,询问人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样来的,走了多久,等等。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是当晚从九寸监视器上看到了他们雪地上磕头的情形。 在我们同处的这条山谷里,铅云欲堕,漫野皆白。一行十数人蠕动在旷野雪地上,双手扬起落下,身体此起彼伏,寂静的山谷中响起了木板摩擦冻土的声响,混合着绵绵不绝的诵经声。貌如印第安部落酋长的父亲桑秋多吉,面部纵横的每一条纹路都刻画着虔诚;英俊的儿子罗布桑布的眼神总是迷茫,总是穿越了现实世界而专注于遥不可及的未来时空。紧随身后的青年僧人嘎玛洛萨、仁钦罗布、江羊文色、嘎玛西珠他们,尼姑英索、江羊卓玛她们,神情都一样的庄重,对摄像师奔前跑后抢拍镜头视而不见。 这一情形经由镜头出现在屏幕上,就具有了瞬间永恒的特质。最初它只被几双眼睛所注视,不久,它就会在西藏、在中国、在大洋彼岸、在地球的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例如,在欧洲的心脏,在戛纳电视节。 由于他们,全世界都将知道了,在西藏,还有这样一种信仰表达方式。 雪域西藏的朝圣行为是从哪个时代起始的呢?从哪一个人开始的呢?为什么要选择五体投地这一含有自虐性质的苦行呢?迄今为止,我没从别一民族、别一宗教、别一地区发现过类似的方式。藏族人认为非如此不能表达最虔诚最深切的情感和愿望。藏族民歌中甚至就有用第一人称描述磕头朝圣的内容,不过未免太轻松,就象浪漫歌谣。歌词很长,大意为——

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 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 陡峭的山崖我象爬梯子一样攀上, 平坦的草原我象读经书一样掀过……
这是一群历时一年多,从家乡囊谦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人。 囊谦在行政地理上属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在自然地理上属横断山脉,在人文地理上属康区,康巴人;在历史地理方面,则是古东女国的腹心地带。迄今古国都城遗址还在。这是我从未到达过的一个县份,依稀听说那里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青海省内贫困县之最,二是该县民众宗教感强极。不知这两点是否互为因果,总之有个数据也许能说明问题:一个数万人口的小县,寺院多达六七十座。 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去拉萨朝圣就既是传统也是时尚。一般人都是步行去,通了公路和汽车,就搭车去。磕着这种三步一身的长头去拉萨朝圣的,古往今来都不多。罗布桑布所在的吉曲乡,上一辈人中有几位老人磕着头到过拉萨。这使他们荣耀了一生。他们的名字也在家乡得以广泛而深入的传诵。这是人们今生钦羡并追求的理想。 正是由于格外的宗教热情的鼓舞,罗布桑布父子久存了这一念头。加之近年间家境不顺,求人打了卦,说是以去拉萨朝圣为吉。亲友们听说了这事,纷纷要求结伴而行。于是由老老少少十八人组成的朝圣队伍组织起来,最年长者是七十七岁的仁增曲珍,第二年长者是仁增曲珍的丈夫、小她十岁的桑秋多吉;最年幼的是不足半岁的贡觉群培,他父亲仁钦罗布是磕头人,母亲阿旺曲珍背着孩子赶驮牛做后勤,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当然是桑秋多吉和仁增曲珍之子、二十九岁的僧人罗布桑布。一九九一年秋季,藏历十月初四日、公历十一月十日,在乡亲们敬献哈达和热情祝福中,罗布桑布一行俯下身去,在山村的土地上磕下了第一个等身长头。从此他们在荒山野地、风雪烈日中就这样行进了一年之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当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磕到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金像跟前时,这支队伍仍是十八人,不过成员有所变化——长达一年一月零三天的旅程中,一些原来的同伴离去,一些后来的人参与,还有一些人来了又走了。他们之中,最年长者仍是仁增曲珍,她七十八岁了;最年幼的仍是贡觉群培,他已一岁半多,在朝圣路上他学会了走路。一年下来,每位磕头人磨穿了生牛皮做的围裙不止八张;用坏了的木制手套不计其数;上路时的十五头牦牛所剩无几。 其实我们早在夏季里就与他们相遇过,只不过是相见不相识而已。八月间我们在德中山沟圣地一起参加了抛哇钦布灵魂迁移仪式,在茫茫人海中他们并未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但我们摄制组三顶颜色鲜艳的尼龙帐篷却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那时他们已磕完了全部旅程的大半,到达了藏北嘉黎县牧区。在那里他们听说了这一宗教活动的日期,就星夜兼程,步行了八天直奔德中。待八天活动结束,又步行八天返回。磕头的进度是缓慢的,最好的日纪录是六公里。差的是一公里。有成员生病、牲畜生病则寸步难行。所以当十月份我们重返这条山沟,居然能与他们再度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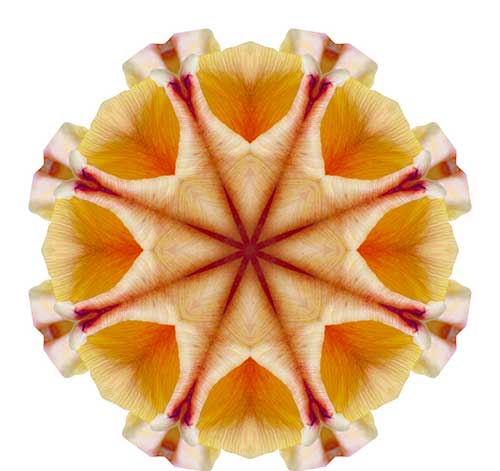
雪绒河是拉萨河的北部上源,我们已沿着接近拉萨河的谷口上溯了六十多公里。公路在这里消失,我们没能继续沿河上行。山谷深处有些什么、山那边有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罗布桑布他们就是从山谷深处磕过来的。据说这是一条古道,古代家乡人去拉萨都走这条山路。到了当代,直贡堤寺下方已有车道可通川藏公路,赶着驮畜去拉萨的行人通常在这里安营扎寨,休息整顿;从拉萨弄来胶皮轱辘的架子车,把驮牛寄存在附近亲友老乡家中,待返回时再吆走。这当然是近些年间的新传统,因为藏地历史上就从不用轮子之类作交通工具。据细心人考察,过去西藏的圆轮形动力器械,就只有法轮经筒这类宗教象征物,民间则只有水磨,车轮是没有过的。 罗布桑布他们已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大队人马原地等待,由少数几人前往拉萨罗布桑布二姐家取来早已准备好的四辆架子车。正准备出发时,前天夜间,他们的几匹马一道走失了。两天来他们沿着河谷去下方找马,往右折进德中山谷去找马。又过了两天,才在上方山谷里找到了马。原来是新近从那里换来的一匹马跑回了原主人家,还裹挟走全部的一群——罗布桑布那天的日记由此而起。 那几天里我们就时常过来串门,随便拍他们的日常生活。烧茶,吃饭,编毛绳,修理磕头用具。年轻好动的僧人们对架子车轮感兴趣,单手抓举。江羊文色、嘎玛洛萨、嘎玛西珠都是一举成功,只有仁钦罗布糟糕,一举再举上不去,很惭愧地让给人家。他的儿子贡觉群培在雪地上走来走去,他妈妈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 能够交谈的只有罗布桑布,他不仅可以用汉语,也可以用藏语的拉萨话交谈。而他的亲友们的康巴话德珍则听不懂。音乐顾问边多老师可以听懂一些。他主要陪梅孩录制桑秋多吉他们唱的歌,是通常僧人尼姑们才唱的道歌。有一首六字真言歌,音乐家们让他们反复地唱了又唱,男独,女独,男女声合唱,歌词就只是那六个著名的音节,曲调却抑抑扬扬,苍苍茫茫,辽辽远远的无休无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