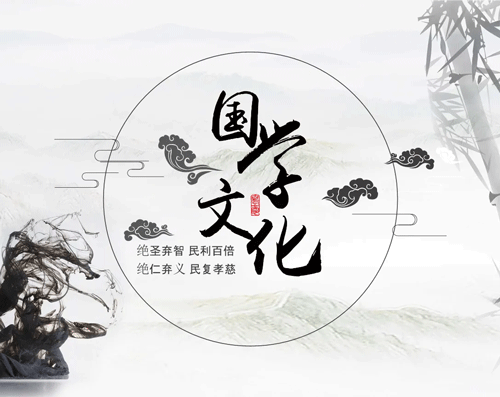隋炀帝杨广,如此昏庸无道,却为何对佛教文化如此重视?
发布时间:2024-07-16 13:03:45作者:地藏网导语:隋炀帝杨广,如此昏庸无道,却为何对佛教文化如此重视?
天台宗的圆融调和色彩。在慧皎所著的《高僧传》中的传主大都是译经大师兼佛典的宣传者。早期的译经大师来自天竺者少,而来自西域(今中亚)者多,从东汉时的安世高(安息国)和支俄(月支国)到东晋时期的鸿摩罗什(龟兹)等都来自西域(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中亚地区,一直被称为西域)。早期佛典的翻译底本多出自中亚语言。直接从梵语译出的佛典,南北朝后期才逐渐增多。隋唐以后,汉译佛典底本才完全出自梵文。正如鲁恭王时发现孔壁引起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一样。直接来自梵文底本的佛学与早期来自中亚语言底本的佛学有很大的差异,因而汉传佛教内部的纷争自隋唐以后开始了,汉传佛教根据不同的判教体系和对佛经不同的理解形成的各个宗派在隋唐时期出现了。
中国古人常以继承方式来创新,孔子“述而不作”即“以述为作”,因而佛学在介绍阶段已孕育着融会的成分。同样,融会阶段也孕育着创造成分。“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颁的理论体系正是凭借《法华经》基本理论框架,大胆发挥其理论创造性完成的。智颁的哲学体系是在对《法华经》的阐释中形成,因而他是从融会走向创造阶段的先行者。北方的灭佛迫使大批高僧南渡,给南朝佛教注入了活力。智领和他的师傅慧思的南下表现了他们对北方政权的失望,也使他们看到了北方佛教发展中的弱点。在南方创宗立派,不仅要获得陈朝王权的承认,又要适应南方思想文化环境,迫使智颁把北方的禅定修行和南朝佛教的义理阐释融为一体,形成其思想学说上的圆融调和色彩,也使汉传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得以在周之际的南朝地区出现。梁启超先生说:“至隋智颁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立`止观之法’,学者以颁居天台,名之曰`天台宗’。其后唐湛然益大弘之。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
智颁的修为和他的圆融调和色彩使他成为当时佛教界的无冕之王。他的思想能为分裂已久的南朝和北朝人民共同接受,这正是统一王朝所需要的思想武器。苏威的“五教”在江南推行中失败,引起江南的叛乱,这使杨广深刻地认识到统一思想的重要性。“天台宗”集南北佛学之大成,在南方拥有深厚的基础,杨广利用智领安抚南人十分成功,使杨素平叛后的南方无大规模的叛乱。另外南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杨广的家传佛教等也是杨广礼敬智频的原因,这两点前人已论述较多,兹不赘述。
尽管杨广重佛轻儒,但儒学历来占据统治地位。以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和凿纬迷信,不但在两汉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在魏晋南北朝也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秦时行法家思想以及汉初行黄老思想时间并不长,梁武帝虽宣布佛教为国教,但同时也非常重视儒学的建设。董、京之流的“天人感应”的儒学和谴纬之学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得荒诞,隋唐儒学的变革必须对“天人感应论”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将它从儒学中清除出去。另外还必须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使儒学增强思辨性以便与佛道抗衡。天下的统一为儒学的反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大儒王通担负起了儒学推陈出新的任务。天人关系的探讨正是王通学说的核心内容,而批判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正是王通学说的重点。
南北朝时期,儒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是西魏苏绰的改革,他在理论界明确地提出了“王道仁政”和“洗心革意”的学说。儒家的正统思想是巩固封建政权的基石,场帝虽然轻视儒学,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在大业四年十月下诏:“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态,宪章文武之道。名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为鼓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隋书·场帝纪)))场帝此举,既笼络了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在“通合儒释”的趋势之下,也有利于统治。

杨广对儒教态度只能说明其政治措施与宗教信仰相悖。杨广对儒学的重视基本停留在表面上,可谓外崇内鄙。他实行科举制度考试设立进士科,以儒家经典命题,但他本身对儒家学说缺乏信仰,只是为了维护统治才这样做的。杨广一生所为,恶迹斑斑,其拭父、蒸母等在后世儒生眼中是大逆不道的。但以佛教“前世因果”等解释是站得住脚的,所谓前世冤家投胎为父子。南宋“天台宗”僧徒志磐说:“世谓场帝察戒学慧,而拭父代立。何智者不知预蕴耶?然能借阁王之事以比决之,则此滞自销。故观经疏释之则有二义:一者事属前因,由彼宿怨,来为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