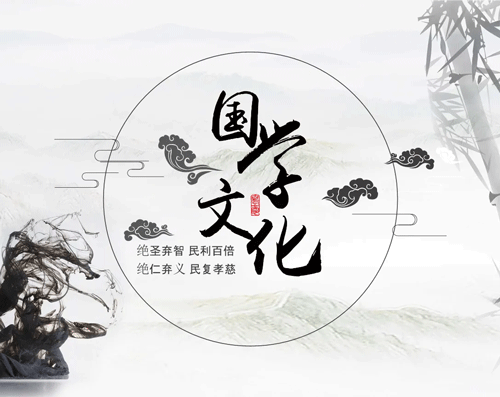音乐·生命·禅境
发布时间:2024-04-12 10:56:39作者:地藏网禅宗认为,心为万物之本,美是心所产生的幻象。只要能悟到这一点。就不致执著于世间之有无得失,就能够摆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达到一种在世而出世间,也世而不离世间的自由境界,其要旨在于"返观自心"。
音乐就诞生、回荡在这种冷寂空无、虚幻深邃的禅境中。
人类通过岩石、花草、树木、水和金属创造音乐的过程,和禅宗通过内在精神活动达到一种超越语言和思想的介不谋而合;它们同样关注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禅宗哲学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死,即死后如何从轮回中摆脱出来,音乐则始终贯穿于人类生命的全部过程。
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几乎包括了人类情感的两极——从肝胆欲烈的痛苦到天国一般的安详。有的是体现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有的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描绘了战争给人心灵留下的创伤;有的是站在历史高度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在他最具有感情深度的第十五交响乐中,音乐家那"命运动机"与朦胧、沉寂主题的相互交替,仿佛是作者向这个曾给他无尽痛苦的世界作依依惜别。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灵》里有这样一幅照片——在空空荡荡的剧场观众席上,孤独地坐着沉思的肖斯塔科维奇。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我老了,死亡临近了,可以说我已经看到了死神的眼睛。"准确地折射出了晚年肖斯塔科维奇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生"与"死"的最后思考。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他深具哲学性构思的著名交响曲《大地之歌》中,对生活、欢乐和期望、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以及最后告别俗世的热情和烦恼描述得入骨入髓。
这可爱的大地/满布春花,重披绿装/在那无际的太空/到处永远放射出蓝色的光芒/永远……永远……
乐曲的结尾拥有一种永恒的奇迹般迷人的力量,当女低音唱着"永远……永远……"一句时,音乐不知不觉间消逝了,它使人感到这乐声是那么之遥远,仿佛已经不在人世而进入"极乐永生"一般--这就是同大地的诀别。我们循着他所创造的意象,也就仿佛和上一次生命相会,又与未来的生命相会。足见,马勒的深刻和伟大之处恰在于完美地表现了永恒,尤其是生与死这个永恒主题。
在中国古代,伯牙、子期之所以成为千古知音,实乃两个生命碰撞的结果,而《高山流水》之为千古绝唱则是自然与生命完美结合的产物。
魏晋名士嵇康遭钟会诬陷被莫名其妙判了死罪后,临刑东市,安详自若地对前来送别的哥哥说:"我的琴带来了没有呀?",哥哥为他取来了琴,他操琴而鸣,奏了一曲"广陵散",深溺乐中,全然无死亡之恐惧。一曲终了,先生抚琴长叹:"想当初袁孝尼先生曾向我学此曲,我太因执而没传授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由是可见,音乐实在是超越社会、自然和生命的大化之境。而稽康先生也就在这音乐化境中涅而永生了。 曾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音乐节上,上演过一位中国作曲家为长笛和打击乐而作的《鼓吟》,作者深谙佛、道哲学思想,认为佛教、道教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超脱精神,从而使他们有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根据庄子的故事创作的《鼓吟》,讲述的是庄子妻死后,烈子去看庄子。烈子见庄子边唱边打鼓,觉得很奇怪,就问庄子。

禅境是无声的音乐。人类在庸常、琐碎、苍白的日子里,压抑、孤寂、幽暗的心境时,常被音乐的光芒照亮,音乐是人类永恒地倾诉,不绝地絮语。当被世俗压抑得气闷的时候,当对岁月流逝感到惊恐的时候,当感到生命的脆弱、茫然与无助的时候,人类都会不自觉地握紧音乐之手。
其实,我们生命的过程,就是在音乐中生活、流浪的过程,许多年以后,我们还会在某支曲子中重现,禅境深遂渺远,音乐深遂渺远,我思想的碎片深陷其中,乏力而无光,也只好如此了。(信息来源:《禅露》)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