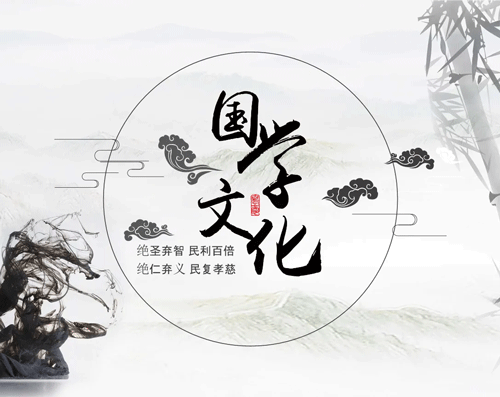依佛法以观人类胚胎(胎儿)的地位
发布时间:2023-10-07 09:47:16作者:地藏网依佛法以观人类胚胎(胎儿)的地位
释昭慧
ㄧ、“生命”之定义与内涵
本文依佛法的原理来阐述“生命”的意义,全文依佛法观点对“生命”作一定义,并简述生命的本质、内涵与出路。
由于生命科技发达,人工流产已更为便利,人类胚胎的利用价值也更为各方之所觊觎,因此本文中将依佛法观点,讨论与人类胚胎相关的伦理争议。
(一)定义
生命,依佛法的语汇,名之为“有情”或是“众生”。有情,梵语sattva,音译“萨埵”,意指具有情感、意识作用的一切生命。这当然不只人类而已,也包括了各种形式的生命。
印顺导师解说“有情”时指出:
“萨埵是象征情感、光明、活动的。约此以说有精神活动的有情,即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小如蝼蚁,大至人类,以及一切有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有情以此情爱或情识为本,由于冲动的非理性,以及对于环境与自我的爱好,故不容易解脱系缚而实现无累的自在。”[1]
有情对自己的生命,有着热烈的情爱,是名“我爱”(?tma-sneha)或“自体爱”,这份爱在空间上扩延出去,就形成“我所爱”(mama-k?ra-sneha),亦即对“我之所有”或“我之所属”之爱,是为“境界爱”。这份爱又可在时间上拉长,本能地对生命的“往后存有”产生强烈的欲求,让生命才死即生,生生不已,是为“后有爱”(punar-bhava-sneha)。
(二)缘起法则与自我中心
原来,一切现象(当然也包括生命在内),都是一连串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迁化而变异、因缘离散而消解的过程。此一和合离散生灭无已的法则,名之为“缘起”(梵pratitya-samutpada)。缘起法则下的一切现象,受因缘左右而变化无已,未曾稍事休歇,是为“诸行无常”法则。一切现象既来自因缘条件的构合,所以生命也就无有常恒不变、独立自存、真实不虚的“我”之可言,这属于“诸法无我”法则。在因缘变迁中,一切现象不但生生不已,也灭灭不已;凡有生者,必趋于灭,是为“涅槃寂静”法则。
然而我爱与我所爱,却形成了“无明”(梵avidya,又名“我痴”,atma-moha)的心理状态。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不能体悟“缘起、无常、无我”的法则;这使得生命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坚固执着,是为“我见”(梵atma-drsti);也使得生命对自己的重视远超过对他者(others)的关注,是为“我慢”(梵atma-mana)。
(三)惑、业、苦三,如环无端
以自我为中心而爱、见、慢、痴发展,这使得生命在知、情、意的三个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扭曲,无法体悟缘起实相。于是,于因缘和合的身心质素上,妄计为“我”,这就使得生命随时随处都依自我为中心——依爱、见、慢、痴以面对自己的处境,并依爱、见、慢、痴以待人接物。此外,又在“无常”的生命与境界上妄计为“常”,产生了对自己身心状况或是周遭人事物境的错误期待。诸如:期求健康不病、期求长生不死、期求他人满己所愿、期求恒有诸乐而不受诸苦……。所求不遂,自然众苦丛生。经中归纳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与五蕴炽盛之八苦;前四者属于生理之苦,第五、六项是社会人事之苦,第七项是境界之苦,第八项总说诸苦的本质:身心的五种质素(五蕴)炽然不息,致令生命流转无已,诸苦由是丛生。
有情无常计常、无我计我,以此计常、计我的心态来面对自己、面对境界,这不但增长了不明事理的愚痴心,而且遇顺境则贪着,遇逆境则瞋恼,此贪、瞋、痴三种心理状态,是为根本烦恼,进而产生了种种大小烦恼(烦恼又名为“惑”)。而这些烦恼又驱使生命造作种种恶身语意业(负面的行为、言语与心念);即便是生起善的身语意业,亦难免为我爱、我所爱之所染污,无法达到纯善之境。这样一来,就在因果法则下,于未来的生命长流里,依其种种善、恶业行,而招感得种种乐、苦果报。
生命并非没有欢乐的一面,而且佛家的工夫论,处处都在教世人离苦得乐,以寻求生命的出路。然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无常计常、无我计我的习性,那么,即使面对那些依善业而招感的欢乐果报,也会产生患得患失的情绪;即便是愉快的心情或欢乐的境界,也会随因缘之变迁而异动,这使得未能体悟无常、无我的有情,感受到无边的苦恼,是名“坏苦”。因此,依佛法来看,越是反其道而行——缩减自我之欲求,多行利他之事业,生命就越是获得喜乐的果报;若能彻底达到“无我”悟境,则更是能印证(终止生命之流转的)解脱之乐。
依自我为中心,惑、业、苦三如环无端。我爱是生命流转的动力因,使得生命才死即生,生生无已。由我爱而产生的烦恼与业,复成为生命升沉流转,具足各种苦乐形态的质料因。生命的形态,一般分作天、人、畜生、饿鬼、地狱等“五趣”。[2]这个生命的环炼无有穷已,必待“缘起无我”的智慧证成之后,方能彻底矫治爱、见、慢、痴之病,断烦恼而得解脱。能臻此境者,名为阿罗汉(梵arhat)。
(四)道德关怀的判准:感知能力
如前所述,佛法将一切有情都视作“生命”,并未赋与人以“仿神肖像之受造者”这样的“神性”。虽然佛典中也提到,人类在知、情、意三方面超越其他生命而有殊胜功能[3],但也并未以此理由,而将其他生命视为成就人类目的的工具。因此对于其他生命(如动物),并不依“神性”或“理性”以为判准,而将它们排除在关怀对象之外。
在某些方面,佛法比较接近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哲学。Singer以“感知能力”为道德关怀的判准,依效益主义而主张谋求(动物在内之)生命的最大化效益。佛法认为,生命都有趋生畏死与趋乐避苦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炽烈无比,因此人作为有道德觉知能力的生命,确实应该依“感知能力”以为判准,将所有具足感知能力的生命,都纳入道德考量,尽己可能设身处地以关怀之。因此佛教规范的根本精神即是“护生”。
以自我为中心既是生命的本能,然则人又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以为他者着想?为何要护念他者的生命处境?在这方面,拙着《佛教伦理学》与《佛教规范伦理学》,以“自通之法”、“缘起法相的相关性”、“缘起法性的平等性”的三大脉络详细阐述其理,[4]为节篇幅,兹不赘述。
二、论胚胎的地位
流转生死中的生命,不外乎是以四种形式出生于人间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此四生的差异是:胎生众生须由母体孕育,待胎体成熟后,方才生出体外;卵生众生则在母体孕育一段时日后,随即排出体外,须在体外孵化成熟方才出生;湿生众生则在母体外排卵受精而成形,部分单性生殖的低等动物亦属于湿生之类;化生众生不须父母精卵为缘,而是依其业力倏忽出生,一般多受生在天界或地狱之中。
由于性别歧视、性观念开放、生命科技研究发展等种种因素,人工流产已出现了日趋泛滥的现象。以干细胞研究为例,从胚胎取得研究用的多能性干细胞,主要来自四种途径:1.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后的胚胎组织;2.人工生殖后多余的胚胎;3.以“体细胞核转植”方式制造的人类或混种胚胎;4.专为研究用而由捐赠的配子制造出来的胚胎。此中除了第三种“体细胞核转植”之外,都有夺取胚胎(或胎儿)生命之嫌。以下将依佛法观点,探究人类胚胎的伦理意义,以及人工流产的伦理争议。
(一)胚胎地位的争议
首先,胚胎(或胎儿)算不算是一个“人”?有否完整的“人格”?应否被列入法律上“人权”的保护?这样的课题,宗教界与科学界的看法就南辕北辙。
依基督宗教“创造论”的观点,人是地面上唯一天主依其肖像所创造的受造物,因此人的生命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可比拟的“神圣性”,任何以人工方式终止人的生命之医疗行为,无论是堕胎、安乐死、人工受孕的胚胎筛检,都是不被天主教廷之所许可的;但这些终止生命的措施若用在动物身上,则因其不涉及“神圣性”被侵损的问题,教廷并无异议。同理,倘能证明“胚胎是人”,则胚胎的神圣性即毋庸置疑。反之,倘若无法证明“胚胎是人”,则胚胎将等同于动物,因其被杀将不涉及“神圣性”被侵损的问题。
然而,即使不是基督徒,不从创造论的神学观点来看待“人”的特殊性,但是反对利用胚胎的阵营,依然可运用义务论,以证成“人”所特有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因为人生来具有“理性”以及伴随理性而来的道德自觉性。亦即:人是“道德能动者”(moral agent)(其实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神圣性”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主张,必须先预设“胚胎是人”的前提。
然而准此以观,胚胎是否可以纳入“人”的道德族群?即不无疑义。因为,就如动物解放之父Peter Singer所言:类似的论证,使我们有理由用在动物、幼儿、智障人、老年痴呆无救者的身上。[5]在同一逻辑下,未必所有的义务论者都会坚决反对利用胚胎。是故基督宗教依神学上的理由,以“人”的物种全面纳入“神圣性”范畴,反而较能坚持其“反对利用胚胎”的一贯立场。
至于目的论(teleology)中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定律——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在攸关“动物权”的争议之中,既可出现像Peter Singer这样(肯定动物与人平等,坚决反对利用动物)的观点,却也可出现“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而赞同利用动物”的观点。同理,面对胚胎干细胞的争议,他们自可依目的论而赞同保护大量胚胎的最大效益;反之,也可依目的论而赞同利用胚胎,以维护大量病患的效益。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说来容易,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要具体地量化以供比较,在技术面是极端困难的。
而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学界人士,依自由主义的观点,从人类胚胎的生物学考量,一口否定胚胎(乃至初期胎儿)等于“人”,理由是:在此阶段,它们尚不具“人形”,也无从拥有相同于人格的道德保护。反对阵营即便是以“潜能论证”(或“连续性论证”),认定胚胎具有发展成人的潜能,从受精卵发展成人的过程不曾间断,因此应享有人性尊严之保障,这依然无法说服他们。因为,从胚胎发展为“人”,须有很多条件的辅助。陈英钤对此做了一个譬喻:
“试想每一个国民都有可能成为总统,……但这并非每一个人都像总统一样享有那么多的特殊保护。而每一个法律系的学生都有可能成为法官,甚至大法官,但在这过程他必须达到许许多多的条件。”[6]
这就如同人皆具有佛性(成佛的潜力),却并非人人都已具足了佛陀功德庄严的微妙报身,道理是一样的。
英国沃诺克委员会(Warnock Committee)建议:胚胎研究可在卵子受精后十四天内进行,因为此时的胚胎发育,尚在二胚层阶段,又称前胚胎(pre-embryo),尚属一般生物细胞,没有神经系统与大脑,故无知觉亦无感觉,不具“人”的道德意义。利用这种体外受精?生的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和临床治疗,并不违反伦理道德。此一观点,已被各国科学家普遍接受了。[7]
(二)胚胎地位的佛法观点
宗教界(包括天主教与佛教)一般的观点都认?:受精卵?生的那一瞬,就已是新生命诞生的始点(starting point);因此,破坏胚囊就意味着扼杀了一个新的生命;胚胎干细胞的分离、研究及应用都是违反伦理道德的。在此,佛教更是可以不去理会“胚胎是不是人”的争议,直下依“众生平等”之理据,强调:不管胚胎是不是“人”,只要它已是“生命”,利用它就有“杀生”的道德之恶。
然则“受精后未逾十四天的胚胎”,是否尚未形成生命?体外培养?生的胚囊,是否就不算是生命?胚胎生命的始点究竟决定在哪里?可以从受精以后的第十五天起算吗?笔者以为,这就如同生命的终点(ending point)落在“脑死”(brain death)一般,实有为了配合医疗科技而“量身打造”的斧凿痕迹,难怪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依佛法以观,生命本身的“我爱”(梵?tma-sneha)与“业”(梵karma),促使了生命一期又一期的受生(佛教称之为“流转”,亦即一般所称“轮回”)。“爱”即我爱,对自我的深固执着,可说是生命受生的第一序动力;其次,生命无始所造之“业”有无量数,但已成熟的业,会成为受生的第二序动力,决定着生命的受生形体与受生处所。易言之,“爱”是动力因,“业”则为质料因。
佛教的经论之中,生命的始点,确实是从精卵结合的一刻就开始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大宝积经》与《瑜伽师地论》[8]在这部分说得非常详尽。兹综合此诸佛典之记载,摘要并以白话叙述如下:
正常的两性生殖,必须具足三缘方入母胎:父缘、母缘、增长感子之业。但是单性生殖(如变形虫、草履虫之类,或是今之复制技术)则不须具足此三缘,直接透过自体分裂,或是“体细胞核转植”技术,即可产生完整而独立的新生命。
正常的两性生殖,在三缘具足之时,入胎众生会在“中有”(梵antar?-bhava)[9]处,见到与自己同类(人类或各种动物类)的有缘父母正交合中,此时入胎众生会产生想要趋近的欲望。它首先对于父母交合所出精血生起颠倒见,亦即:不知这是父母交合,而起颠倒性的认知,认为是自己在与对象交合,由是而生起贪爱。这时若它将生为女胎,就会对父亲生起交合的贪欲,希望母亲远去;反之,假使它将生为男胎,就会对母亲生起交合的贪欲,希望父亲远去。(这一点,或许可解释女儿的“恋父情结”或儿子的“恋母情结”是从何而来的)。
有了这种交合贪欲,入胎众生就只会见到自己想要交合的对象,这样渐渐趋近父母,渐渐地,不见父母的全部身体,只见到他们的“男女根门”(生殖器),就在这里被“拘碍”起来(进入子宫)。
当父母交合至“贪爱俱极”时,最后将“各出一滴浓厚精血”(亦即各出精卵),二滴和合(亦即精卵和合),住母胎中合为一段,犹如熟乳凝结之时。当此之时,“中有”即灭,入胎众生的识已住于“结生相续”(亦即:就此产生了新一期的生命),从精卵结合的一瞬间开始,连续七天,名为羯罗蓝(梵kalala)位。即由此与胚胎俱生的“诸根大种”(应即未分化成特定组织或器官之前的多能性干细胞)之力,眼等诸根(器官)将次第而生。
又此羯罗蓝由色(物质)与心、心所(即心的附属功能)相依俱起,由心与心所的依托之力,使得胚胎不会烂坏,色、心二者“安危共同”,而且“平等增长,俱渐广大”。显然,羯罗蓝是心识的最初依托之处;亦即:在精卵结合的那一瞬间,心识已经入于其中,新的一期生命也就以那一瞬间为其“始点”了。
入胎众生在胎藏之中,历经八个阶段。每一阶段胞胎的成长情形,《瑜伽师地论》中均作解说[10],八位如下:
1. 羯罗蓝位(梵 kalala),译作凝滑。指受胎后之七日间。
2. 遏部昙位(梵 arbuda),译作疱结。指受胎后之二七日(十四天)内,此时其形如疮疱。(以上二位,即是受精后十四日以内,亦即当前法令许可取得合法胚胎干细胞的时限)
3. 闭尸位(梵 pesh?),译作聚血或软肉。受胎后之三七日(二十一天)内,其状如聚血。
4. 键南位(梵 ghana),译作凝厚。受胎后之四七日(二十八天)内,其形渐渐坚固,有身、意二根(“根”即感官),但是尚未具足眼、耳、鼻、舌四根。
5. 钵罗赊佉位(梵 prash?kh?),受胎后之五七日(三十五天)内,肉团增长,始现四肢及身躯之相。
6. 发毛爪位,受胎后之六七日(四十二天)内,已生毛发指爪。

7. 根位,受胎后之七七日(四十九天)内,眼、耳、鼻、舌四根圆满具备。
8. 形位,受胎至八七日(五十六天)以后,形相完备。
入胎众生若是人类,在母胎中经三十八个七日(亦即二百六十六天),这时胎藏中的一切支分皆悉具足。从此以后,复经四日方得出生。这是最极圆满的住胎方式。有的经于九月、八月就会出生,这尚可名“圆满”,但并非最极圆满。若只经于七月、六月就出胎,那就是比较危险的早产现象,不名为“圆满”,身体的健康情况容或有所“缺减”。
由于凡夫众生会在自体上执为“我”(梵?tman)与“我所”(梵mama-k?ra,亦即“我所属”或“我所有”之意),由是而生起“我慢”(梵?tma-m?na,重视自己,相对地也就较不重视他者),因此圣者观此生命会因我执而产生种种痛苦。但是另一方面,处于胚胎状态的众生,因为觉知苦乐的感官尚未育成,所以只有“不苦不乐受”(梵aduhkh?sukha-vedan?)[11]。在这方面,佛典所说,确如今之医学界的看法。至于苦受或是乐受(亦即觉知苦乐)的能力,则必须待到胎儿的支分(分化组织与感官)具足,并配合使其受苦受乐的境界因缘,方能生起。
虽然佛典亦已证明:初期的胚胎由于支分未具,并不能觉知苦乐,但这并不表示,利用这些胚胎不会具足“杀生”要件(至于胚胎是不是“人”?具不具足“人”的内在价值?这些争议可先暂置一边)。例如:昏死过去的人或动物,同样无法觉知苦乐,但令其断命依然犯“杀生”过,毁损胚胎的情形是类同的。
(三)伦理抉择的两难课题
综上所述,佛教对胚胎生命的看法是:胎生众生的一期生命,主要来自于父缘、母缘与亲子因缘;入胎的近因,则来自其淫欲心。在佛法来看,淫欲心非善非恶,属于“有覆无记”(亦即:虽无善恶之记别,却会覆障真理);淫欲心又是来自“我爱”(梵?tma-sneha)与“无明”(梵avidy?)。职是之故,并无理由足资证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但是,胚胎生命是否已具足目的性而非工具性意义?答案则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期待它存活下去的,已不只是父、母亲等旁人对胚胎的主观意愿而已,更强烈的期待来自入胎众生本身因我、我所执所产生的,本能的自体爱。
这份自体爱,纵使是在无法觉知苦乐的状态之下,依然发生强烈的作用——使得生命“结生相续”,而且使得胚胎在母腹之中,一直保持色心互依,不烂不坏且增长广大(亦即增生复制)的状态。只是由于一般人无法目睹,所以销毁胚胎较之杀害动物,更不易激发起人们的同理心(亦即佛教所称“自通之法”)。
职是之故,撇开胚胎干细胞研究对人类的工具性价值不谈,当前医学界的动物实验是如此频繁而大量,实验动物的命运又是如此悲惨,胚胎干细胞研究或可使得动物实验的需求量减少,这样的讯息,必然使得强烈主张“不杀生”(不管是人、非人,都不可杀)的佛教,都不得不面对了伦理抉择的两难课题。
试想:一个服膺“众生平等论”[12](而不是“人类神圣论”)的佛弟子,当他面对着伦理抉择的两边,一边是无有觉知能力的人类初期胚胎,另一边是有血有肉、有觉知力,且会呈现苦乐之丰富表情的动物,如果必须要他选择“放弃一边”时,他会放弃哪一边呢?
当然,彻底奉行“不杀生戒”的佛弟子,必然会选择“两边都不放弃”;亦即:坚持无论是取用胚胎还是动物作为牺牲品,都是违背道德的。生命(当然也包括胚胎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内在价值,不来自其神学上的神圣性,也不来自其“理性”或道德自觉能力,而是来自每一生命无可替代的主体性。主观上,每一生命(包括动物在内)都不容他者将自己当作非自愿性的牺牲工具,来达成他者的效益。在这种考量之下,遵行“不杀生戒”的佛弟子,心态上毋宁是倾向于“杀一不辜而不为”之义务论的。
三、结论:“缘起中道”的工夫论
如上所述,佛教的生命观,是建立在“缘起”法则下的,它既面对着生死的无常变化,又无有独存之“我”可言。若未能勘破无常与无我,则生命必然依惑、业、苦之流转而滋生种种忧悲苦恼;反之,多行无私利他之事,生命则多得福乐;若能彻悟无常、无我,则生命能得究极解脱的喜乐。
众生在缘起法则下,是因缘相依而法性平等的。众生既然都有感知能力,也都同样趋乐避苦、趋生畏死,因此吾人宜平等考量生命(而不只是人类生命)的利益。消极方面不恼害众生,积极方面,甚至要救护众生。
至于胚胎或是胎儿,依佛法来看,即使其是否等同于“人”的定义尚有争论,但其确是“生命”,则并无疑义,因此不宜以其不具足“人”的位格,而就轻易人工流产。至于受孕后十四天内无有苦乐感知能力的说法,如前所述,佛经指出:羯罗蓝(梵 kalala)即受胎后之七日间,遏部昙(梵 arbuda)即受胎后之二七日内,此二位,即是受精后十四日以内,亦即当前法令许可取得合法胚胎干细胞的时限,其时胚胎凝滑而如疮疱,自是没有苦乐感知能力。这方面,与科学界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依佛法的生命观,虽然尊重生命趋生畏死的本能,而重视“护生”的实践,然而生命又从来不可能免于相互的伤害,现实情境时常会逼到人们非“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例如:人们可能要在“维持动物实验”与“允许有限度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二者之间放弃其一。即使在最素朴的情感层次,基于“自通之法”(同理心),人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能够觉知苦乐的广大病患、人体实验之受试者以及悲惨的实验动物之处境,而绝对站在无觉知苦乐能力的前期胚胎这一边吗?
再以“不杀动物”为例:主观上佛弟子当然不希望任一动物被杀,但是这份理想即便是要落实到生活之中,那么,最严谨服膺“不杀生戒”的佛弟子,尚且不能免于在呼吸、喝水、进食、医病的过程中,伤杀微细生物与寄生虫;即使秉持最严格的“素食主义”,也不能免除农夫在种植蔬果时,垦土掘地或喷洒农药对众生所造成的伤害。在个人自主的情境之下,有道德理想的佛弟子,尚且无法百分之百“戒杀”,然则侧入公领域之时,面对广大社会与各方利益,个人自主的空间就更有限了。
有道德理想的佛弟子,即使无法百分之百“戒杀”,也必须坚持其余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的“护生”努力。同理,侧入公领域之时,面对广大社会与各方利益,佛弟子难道可因攸关“动物保护”的法律与政策之制订,无法百分之百达成“戒杀”理想,而就通盘放弃在其余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乃至百分之十的影响力吗?依笔者的经验,我们选择的不是道德洁癖式的“不介入”,而是“强力介入”;即使最后订出来的动物保护相关法规,离我们的理想尚远,但是我们永不会放弃施加任何一点的影响力;即使是渐进而缓慢地以慈悯不杀的理念,少分影响着法规的品质,那也好过完全放弃此一努力。
显然在理想层面,我们可以孤悬“一点都没有打折余地”的“不杀生”规范;但是在实践层面,佛法还是要有一套“行动哲学”的。即使是佛陀也不例外——他一方面坚持“不杀生”之规范,一方面也不得不因托钵的条件限制,而允许“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而杀”的“三净肉”。
这就是“缘起中道”(缘起:梵prat?tya-samutp?da;中道:梵madhyam?-pratipad)的智慧,笔者曾将“缘起中道”的行动哲学定义为:在有限的因缘条件下,无私地作出相对最好的抉择。面对缘起法则下生灭不已的生命,吾人要倘具体实践“护生”的理念,必须依“中道”以为实践原则,尽己所能以达到“相对最好”的效果。这就是“护生”在现实环境中的实践要领。
九三、七、十八 于尊悔楼
——摘自《辅仁宗教研究》第十期(2004冬季号)
[1] 印顺导师:《佛法概论》,页43-44。
[2] 犊子部则加阿修罗之种类而分为“六道”。“六道”后来成为大乘佛教的通说。
[3] 人类之“三事胜诸天”,语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172引经(大正卷27,页867下)。以上三事内容解明,参考印顺导师如下诸文:一、〈人性〉(《佛在人间》页88-94)。二、〈从人到成佛之路〉(《佛在人间》页132-3)。三、《成佛之道》(增注本)页48-9。四、《佛法概论》页50-54。
[4] 释昭慧,《佛教伦理学》,页75-86,台北,法界,民87,三版;《佛教规范伦理学》,页84-93,台北,法界,民92。
[5] Peter Singer着,钱永祥、孟东篱译,《动物解放》,台北:关怀生命协会,1996,页64~65。
[6] 陈英钤,〈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管制〉,《第三届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论文集》,页I-11。
[7] 丘祥兴,〈人类干细胞研究的若干伦理问题〉,《第三届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论文集》,页H-7。
[8] 汉译经律论中,以下几部典籍对这方面所载最详:《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一(大正24,253中~256中),《大宝积经》卷56-57(大正11,328中~333上),《瑜伽师地论》卷1~卷2(大正30,282下~285中)。其中《瑜伽师地论》提及,其所陈述引自佛说的《入胎经》。
[9] 亦即一般所称的“中阴身”,即前世死之瞬间(死有)至次世受生之刹那(生有)的中间时期。中有之身,唯于欲、色二界受生者有之,于无色界受生者则无此身。在部派佛教,“中有”有无尚存异议:说一切有部主张中有实存,分别说部及大众部则认为中有无存。
[10] 胎藏八位,详见《瑜伽师地论》卷二:“若已结凝,箭内仍稀,名羯罗蓝。若表里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昙。若已成肉,仍极柔软,名闭尸。若已坚厚,稍堪摩触,名为键南。即此肉抟增长,支分相现,名钵罗赊佉;从此以后,发毛爪现,即名此位。从此以后,眼等根生,名为根位。从此以后,彼所依处分明显现,名为形位。”(大正30,284下~285上)。
[11] 《瑜伽师地论》卷二(大正30,284中)。
[12] 何以“众生平等”?这方面的辩证,详见拙着《佛教伦理学》第二章,台北:法界。